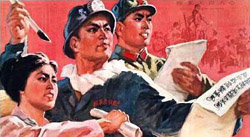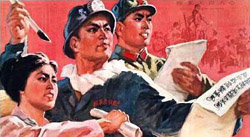 |
无 产 阶 级 文 化 大 革 命
无 产 阶 级 专 政 条 件 下 的 继 续 革 命!
|
Important Notice: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our free phpBB forum hosting service will be discontinued by the end of June 30, 2024.
If you wish to migrate to our paid hosting service, please contact billing@hostonnet.com.
|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 作者 |
留言 |
hgy818

注册时间: 2007-09-13
帖子: 1298
|
 发表于: 星期三 十月 24, 2007 7:55 am 发表主题: 巨变时代的世界观——《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摘要 发表于: 星期三 十月 24, 2007 7:55 am 发表主题: 巨变时代的世界观——《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摘要 |
 |
|
巨变时代的世界观
——《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摘要
张汝伦 汪晖 等
主办: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地点:上海,图安宾馆
时间:2007年6月30日
《读书》与近二十年中国与世界的巨变
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最近十年来,关于《读书》有很多说法,我想将来中国思想史可能也会去研究这个现象。在我看来,《读书》是唯一的,它对中国问题、对世界问题关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反映的及时和迅速,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白纸黑字在那里。首先请文选的主编汪晖先生来谈一谈他编这套书的想法。
汪晖(清华大学教授、《读书》杂志主编):我们很早就有编选这套书的想法。我和黄平大约是从1996年参与到《读书》的编辑工作中,到现在也有十年的时间了,编选这套书的过程让我们有机会对这十年的工作做一点回顾和反省。我们也在想,为什么《读书》会引发那么多的争议?中国社会在1989年以后发生了很重要的转变,最初的几年相对来说是比较沉闷,但也比较沉静,我参与编辑的《学人》丛刊大致可以反映那个时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知识界的重要变化大约是从1994年、1995年开始的。我举两个主要的例子,一是关于“人文精神讨论”,这是在《读书》上发生的;二是在《二十一世纪》上发生的围绕着苏东改革、自发私有化问题,尤其是如何判断叶利钦改革的讨论。崔之元写了《制度创新和第二次思想解放》,又与昂格尔合作写了《以俄为师看中国》,算是对苏东改革特别是叶利钦时代做出的第一次正面反思。与此相关的,有王绍光和胡鞍钢的“国家能力的报告”引发的争论。
这些思想变化包括两重背景。一是我们都曾为之欢欣鼓舞的邓小平南巡显示出它的双重后果:在国内方面,新一波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从社会分化、制度性腐败到潜在的危机。在新的条件下,我们不太能够将这些问题简单地归结为过去——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历史。在国际方面,1993年秋天,叶利钦命令军队炮击议会,那时美国的舆论一边倒,认为这是针对前共产主义分子的捍卫民主的行动。俄罗斯危机使民主和民主化从一个自明的价值目标,变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究竟怎么去理解民主,我们要的是哪一种民主?在1990年代初期,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把俄罗斯改革看成是中国的楷模,但随着俄罗斯危机的爆发,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开始了。我们在《读书》杂志编辑过程中,有意识地把这类问题提出来。1996年《读书》开始了关于乡村的讨论,后来又开辟了“田野札记”这样的栏目,虽然当初的思路是模糊的,并没有后来“三农危机”那样清晰的意识,但的确提供了一个通往后来的讨论的基础和前提。
不久之后,《读书》也展开了关于苏东问题的讨论,秦晖和金雁给《读书》写过稿,黄立佛等研究俄罗斯的一批学者也写过。蓝英年和张洁各用档案来说明苏联时期的文学与文化政治,但取向和结论却各不相同。你会发现围绕这类问题展开的争议,最终总是会涉及如何看待二十世纪的历史。我记得,那时候何清涟也在《读书》上发表文章批评经济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包括几位经济学家激烈的辩论。这些辩论的水准不能说很高,但情绪相当激烈,显示讨论触动了尖锐的问题。正好在这个背景下,在1997年、1998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所谓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我始终不认可这个二元框架——这个框架不但将复杂的思想讨论简化为两相对立的图景,而且也引发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讨论,后者的结果就是将讨论变成讨伐和攻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时期的辩论几乎涉及所有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国际等等均卷入其中。在中国知识界发生剧烈变动的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情绪的激烈化,简单的命名是导致情绪激烈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读书》希望展开的讨论,发出代表不同声音的文章,产生真正的争论,但有时候情绪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争论——如果专注于问题,有点情绪其实也算正常。
另外一个脉络,也是在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有关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的一些理论介绍进入中国,使我们有一个感觉: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知识图景是片面的,世界图景也是片面的。其实,早几年,《学人》丛刊就已经在反思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学术思想传统的问题。过度的西方化,严格地说,过度美国化,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我们谈论西方,但很多人连欧洲也不是真正了解,东欧、俄罗斯等等就更不要说了。在我编辑的《读书》的第一期中,即1996年5月号的开篇,我们开始了有关“亚洲意味着什么?”的讨论,此后十一年,我们的讨论从日本、韩国、港台地区扩展到东南亚、南亚、西亚,与关于苏东改革、拉丁美洲问题、欧洲统一问题及美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等等的讨论相互配合,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中国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涉及历史观的转变,世界图景的转变。我们过去总是说改革开放,但你怎么定义这个“开放”?实际上,我们对西方世界,尤其是对西方世界之外的地区,缺乏真正了解。
只有当乡村的问题、社会分化的问题,以及当代世界的复杂图景在讨论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对我们习惯的那些思想图式加以反思,比如现代化意识形态中有关市场与国家的表述。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很多人认为市场化不但可以解决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但究竟怎么来理解市场,争议是极大的。在这类问题上,你会发现,左的和右的,都是价值先行,对市场本身的历史分析相当不够,对国家的分析也同样如此。在今天,随着利益分化,国家权力与利益集团的内在勾连,作为总体的国家概念已经难以描述市场化和全球化条件下的复杂的国家活动了。换句话说,国家虽然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但国家在整个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经常是分裂的,中国知识界并没有提供新的理论范畴、概念和描述。
最后我回应一下张汝伦先生说到的争议。除了就贫富分化或者涉及我们日常生活的话题,跟我们日常生活并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也常常引发激烈争议,这是我们过去很难想象的。比如科索沃战争、美国“9·11”事件、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如果说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直接地触动了中国人的心弦之外,这一系列与中国无关的事件为什么会在中国知识界内心深处产生如此剧烈的冲击?这是少见的现象。这说明什么?说明整个二十世纪形成的情感,在危机时期产生的判断,在所有历史事件中都会爆发——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危机即使与我们距离遥远,我们也并不难判断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后来《读书》展开的很多讨论,在海外也连续发生反应,形成对国内讨论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文选本身能从一定侧面回顾十年中国知识界走过的道路。
叶彤(《读书》杂志编辑):这套书有两百多万字,是《读书》十年所有发表文章的十分之一多一点,也是《读书》十年严肃的小结。我参加编辑《亚洲的病理》,感觉这些文章是知识界共同营造的一个结果。有人批评《读书》,说文章不好懂。其实坐着看和躺着看,是很不一样的。整个社会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人们的知识结构也有很大变化。《读书》上发的很多文章也是属于“新知”,无法让所有人都觉得很好读,很愉悦,很舒适。编辑部内部有过非常多的讨论,几乎每编一期都会反复权衡:这一期是“软”了还是“硬”了?是不是不好读?是不是太重?但你必须在“可读”和内涵之间做一个选择。也许这篇文章确实很“好读”,可相对而言问题不是那么重要。而另一些文章中的问题确实重要,但文章写的不够好,这就需要做出选择,需要编者与作者磨合。作为一个编辑,我也承认《读书》的有些文章不是那么“好读”的,读起来确实需要一些功夫。我们编辑要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与作者做更好的沟通。
王晓明(上海大学教授):从创刊起,《读书》就有几副面孔:一个是文学化的,谈文论史,比较文人气;另一个是政治性的,直接去触碰当代的思想、社会以及文化问题的,比如创刊号上的《读书无禁区》就鲜明体现了后一副面孔。《读书》这后一副面孔一直没有变。我个人记忆最深的,是1993年冬天我们在华东师大讨论“人文精神”,满满一屋子人。我事先联络了沈昌文,他就和吴彬坐飞机来听,回去后来信说《读书》支持这个讨论,于是就有了一连五期的系列讨论。我今天重提这件事,是要说《读书》有这样全国性的声誉,还有了国际影响,主要就是因为它有这一副面孔。不管今后谁编《读书》,如果这一副面孔没了,就是销路再大也是失败。《读书》不是《读者》。
有人批评这十年《读书》的文章太“社会科学”了。我也有这个感觉。怎么看这个变化?还是拿我个人为例:最近十年,我给《读书》投稿不如1990年代多。因为国际国内的社会变化太大,看不清楚。原来那一套比较简单的世界观不够用了,需要学习大量新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写得少,不敢那么文学化地洋洋洒洒,也就很自然。从这个角度说,《读书》文风的改变,其实反映了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整体思想学术状况的变化。一本杂志能有这个代表性,恐怕正是杂志的成功。一个大国处在剧烈变动时期,如果不能有一个让各种思想和学说自由讨论的空间,是很危险的。如果这样一本标志性杂志被改成一本无关痛痒、只是发发小牢骚、发发小感慨乃至风花雪月的杂志,那就太糟糕了。
蔡翔(上海大学教授):我是《读书》的老读者,也是老作者,应该说对《读书》的感情是非常深的。这十年,就像汪晖刚才所说,是中国知识界大动荡的十年,不仅知识分子在进行激烈的辩论,许多杂志也都介入了公共领域里的讨论,而我觉得在这些杂志中,《读书》始终走在思想探索的前沿。我觉得在中国社会激烈的变化中间,《读书》能够始终和现实保持对话,而且主动介入许多重大思想问题的讨论,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点上,我以为它秉持了《读书》的一贯传统。
当然,在这十年中,《读书》对公共问题的关心,更多地是通过知识和思想层面的讨论,来展现的。过去,我们有些讨论过于情感化或者道德化。不是说情感不重要,没有情感的介入,所谓“知识”就仅仅只是“知识”。但是,仅仅停留在情感层面,许多问题就很难深入。《读书》的讨论常常是在知识层面上展开,而且提供了各种专业知识的背景,这也是我读《读书》常有很多收获的原因,而且我也希望今后的《读书》能够继续朝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如果这样一种发展变化导致了所说的读得懂读不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用“好看”来要求《读书》,这一要求就实在太低了。而且,《读书》三十年的传统也不是所谓的“好看”就能概括的,三十年来,《读书》一直致力的就是传播新知、关注历史和现实、积极探索中国的未来。所以,它不仅成为中国知识界最著名的思想平台,同时通过思想的传播而在中国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知识群落。我以为,这才是《读书》最重要的传统。
高瑞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我算是《读书》的老作者和忠实读者,我认为刚才晓明对《读书》两个阶段有一个比较公允的评论。1980年代的《读书》和近十年的《读书》,其实也不完全是时间的问题。前者是专家写给热心于这些问题的外行看的,而后者可能更多的是专家写给专家和近乎专家看的。另外一个差别,我感觉1980年代的《读书》常常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边缘行走,但是像刚才晓明说的,可能那个时候市场比较简单,或者说那时候变动刚刚开始,专家们可能对文化方向或者我们的时代没有很多困惑,觉得自己的目标很清楚。到了1990年代,巨大的变化发生了,对时代的认识成为时代的问题。其实这种情况在1920年代、1930年代、1940年代都出现过。我前段时间看《观察》。《观察》有篇小文章讲“时代”,用了十几个名词,就是没法用一个统一的名词。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就在巨变中。但在当时比较短的时间内,我们觉得我们走进新时代了,觉得没问题了。现在我们知道自己的方向感并不明确。我在一次讲演中也讲到,中国哲学研究现在完全失去了对时代的把握,有时被当作某种知识背景,被用来个人修身养性,但它就没有对这个时代的把握。我觉得《读书》在这十年确实是触摸了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希望以后继续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就个人经验而言,我倒是觉得1980年代的《读书》蛮难读的,流行学术新名词大多是1980年《读书》发明的。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他们谈“20世纪中国文学”,里面好多词呵,什么能指、所指、共时性、历时性,大家知道得特别少。到1990年代留学回来,因为自己受过训练,不管我同意不同意某些文章的观点,但我觉得它们特别明晰,整个论证的展开对我来说更为有效。可能是问题很复杂,如果要有效展开,就不能不借助很多理论资源。但这带来一个问题:如何在通俗层面谈问题?这样,《读书》就变成一个——我相信这不是主编的意图——文人圈子,或者说同行写给同行看的东西。中国共同话语空间出现了一个断层。在理论的有效性和复杂性之间,怎么样做一个取舍,我觉得这是《读书》面临的考验。1980年代能够感知到的问题相对简单,容易用一个好像专业说给外行的方式谈,但是1990年代这个方法不再有效了,至少对专业之外的知识大众来说,他们会有他们的问题。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1980年代,大家的眼界和世界图景,总体来说还比较单一和整一,知识界能够统合起来,《读书》也就统合了各种各样的资源,表现出一种态度、立场、观念,甚至是文风的多元统一性,也就是晓明老师讲的几副面孔。那当然是个值得怀想的年代。但是如今,现实发生了剧变,知识界开始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知识背景、现实立场以及写作趣味,与此同时,市面上也已经有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报刊。因此,即使你想回到1980年代一本《读书》一统天下的时代,也不大可能了,我个人甚至觉得,《读书》眼下也不必、起码不必过于追求这一点。倒是《读书》创刊二十八年来,一以贯之的中国关怀与知识关怀,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所以,我想接着张汝伦老师所说,近十年来的《读书》是更加唯一的,因为就像厚厚六本书明摆在那里的,在深刻介入中国当代的社会与文化问题,在全方位呈现新的历史与知识时空等等方面,这十年的《读书》都居功至伟。也因此,它的影响可以说是国际性的。
换句话来讲,如果说《读书》也的确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困境的话,其实,那更是当下中国的问题和困境,特别是知识界的问题和困境。比如,不少人说的“文学艺术类的文章比重下降”问题,就很大程度地因为蔡翔老师一直在讲的一个原因:1980年代中国是文史哲和心理学勃兴,而到了1990年代,则大有社会科学化的趋势,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开始成了主导性的学科。这多少也因为中国和世界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必须以知识化的讨论才能够应对吧。而且事实上,假如有一定的知识训练,你可能反而会觉得这类文章有来路,有学理脉络,容易把握,不是“看不懂”的。
当然,文学、艺术以及文化这些“轻”的领域,是格外牵涉到人的情感结构和感性活动,更为深刻地表征了一个时代的,而且它们对于年轻学生和普通读者的影响力更大、更强。因而,如何抓住他们也实在是非常重要。这,或许应该算是我们对《读书》的更高期许,而不能成为否定《读书》的理由。
雷启立(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深刻地卷入到中国这十年来的变化中间的,在一定意义上,它形成了某种权威,不是那个威权意义上的权威,这在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今天是非常可贵的。比如说,汪晖谈到,《读书》在九十年代中期就讨论的三农问题,今天农民问题至少被作为话题在讨论,新农村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个局面的出现不能不说与以《读书》为主体的知识群体的关注相关。《读书》六大本里面所牵扯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曾经是遥远的问题,但是,今天是非常深刻的现实问题,或是造成严重后果的问题,比如说环境问题,比如说大学的理念、学科化的问题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里面知识共同体在用知识的方式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对这个社会发言,《读书》在这个十年中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读书》的话,这个中国还有哪些地方会发这样的声音,能起这样的作用。它凝聚了在这十年中间不断被边缘化的知识和思想的尊严和力量,有些甚至逐渐形成社会共识,对社会文化的变化产生作用。近十年的《读书》一直发行量很大,有人看有人想,有人看不懂,生气,不管怎么样,它使自己关心的问题成为有效的真问题,把被边缘的东西拉向中心,把被遮蔽的问题彰显出来。当一个社会过于偏向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拉扯的力量。
所以我说,近十多年的努力,《读书》杂志与学院知识有连接却并不学究,尽可能快地对社会现实的变化作出一个知识群体所可能有的反应——虽然不一定都怎样深刻,却为日益科层化的学院知识群体提供了“有机”的可能;不让思想和知识的多种面向为西方主流理论所遮蔽,尽可能丰富地引入和彰显各种还在边缘的甚至不入流的思想和言说——而这些思想和言说对于应对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不让知识和理论为某一个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所占有和利用,而是尽可能深入地让知识和思想渗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作用——事实上也对社会文化的变化产生了主要作用,使不少被遮蔽的问题浮出了水面;不是局限于某一个阶层或者仅仅是中国人的立场提出和思考问题,而是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大国的知识群体对于各种具有世界性的问题所应该有的宏阔视野和对“他者”问题的关心。——一句话,它表现出了一个负责任的知识群体的刊物应该有的样子。
戴锦华(北京大学教授):读得懂读不懂的说法,在当代中国是个有效的攻击武器。说不懂的人未必不懂,这本身是一种姿态,一种攻击性手段。这种说法其实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此前是“工农兵文艺”,以人民的名义要求你明白晓畅,喜闻乐见。然后在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做了一次偷换,把借助人民的合法性,偷换成大众文化的合法性,要求你通俗易懂。我想,《读书》一开始就不是让人躺着看的。它到什么时候变成躺着看的了?什么时候又坐起来了?什么时候又站起来了?文学的比重是另一个问题。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扮演着一个何其超载的角色,它承担着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现实介入、社会批判等功用。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造就的,有1950到1970年代包括“文革”造成的历史成因:全民扫盲文学普及、群众是个运动,也许还要加上全民学哲学和用哲学。正是这样的历史前提下,文学和关于文学的讨论才可能呼唤出巨大的读者群。这种情况到1990年代已完全改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结构变化。恐怕我们首先要谈历史、现实、特定的时刻,社会结构,然后我们再来谈一个杂志、一种文风、一种语言、一种书写的可能。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读书》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好看不好看。问题是制约《读书》的背景性条件发生了太大变化。这些变化至少有三:第一是公共文化界的消失。1980年代有一个统一的文化界,提的问题很难用某个学科来限制,大家读的书都差不多,你读过的我也读过。但到了1990年代以后,公共知识界解体成为一个个所谓学科,虽然有些文章谈的是公共问题,但操的都是一些自己行业的“黑话”,你不在这个行业就很难看得懂。读者本身也被专业化了,这是一个大趋势。第二是1980年代曾经有过的宽松环境如今荡然无存,好多问题成为了禁忌。当你试图表达什么的时候,问题不在于说什么,而是怎么说,越是专业化的表达,越是具有某种表达的自由。最后,1980年代有一个启蒙的基本共识,即使观点分歧,背后也有基本的共识,即汪晖所说的“态度的同一性”,对现代化的同一态度。但这些共识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消失,分化为各种意识形态、各种专业知识学科,甚至彼此难以通约的小共同体。专业分化可以说是一种知识成熟的表现,但意识形态往往会流于情绪化。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这些年《读书》的话题发生了转变,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和1980年代相比,杂志面临的语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譬如文化中心已经集中到某些大城市,而且这些大城市的文化具有某种支配性地位,所以读者和话题也往这方面集中。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要讨论读得懂读不懂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衡量标准,就是看内地的小知识分子,比方中小城市的中小学老师,他们还读不读《读书》?或者说他们读了《读书》之后的反应怎么样?像《读书》曾经好几次讨论过话剧,但这些话剧在内地根本看不到,即使在大城市演出,昂贵的票价仍然是让人望而止步。所以《读书》花那么大力气讲赖声川的戏剧,讲田沁鑫的《生死场》,许多人根本看不到,因此很难与讨论发生直接的、内在的联系。
这样说也许有点苛刻,但这一现象表现了一种文化语境的变化。199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读书》的作者和读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到了大城市里,很多人都在高校里教书。武汉、兰州这些本来很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开始衰落了,因为北京、上海以及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把那里的人才像抽血般地吸引过来了,更多的青年学生则通过考研究生啊、找工作啊……也向大城市集中。这样一个人才大规模流动和文化中心的聚集,是《读书》这些年来不得不面对的背景。《读书》可以在知识上、理论上讨论这个流动的问题,很多有反思性的话题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但问题的严峻性在于,《读书》本身实际上也处在这个过程之中,甚至这些年来由它引发的一系列讨论也可以看作是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症候”。那么,《读书》应该怎么办?我觉得看得懂看不懂的问题,要和理解场域发生深刻变化联系在一起分析,才不会停留在低层次,才能更有生产性。
看得懂看不懂的问题,还涉及到另一个理解的场域,那就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崛起的互联网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讨论中,网络的作用非常大。就拿我最近常常去看的“闲闲书话”来说吧,那里当然是以批评《读书》的言论为多,但有趣的是,第六期《读书》甘阳的那篇文章一出来,马上成为话题,引起讨论,甚至挨骂。其实骂也是看过了,看过了才能骂,不看怎么骂呢?所有《读书》的一举一动在网络上都可能引起很大反响,证明它还是被广泛关注的,这是《读书》相当宝贵的财富,当代中国恐怕没有一本思想性的杂志可以得到如此高的关注性,因此,《读书》和网络的关系,值得好好讨论。
戴锦华:1980年代初有一本杂志大家肯定都知道,叫《大众电影》,曾经发行到几百万份,但如今只剩了几万份,举步维艰。《读书》从1980年代到今天,它的订数是多少?基本稳定,甚至还有上升。可见在1980年代《读书》也不是大众媒体;也可见得在大众传媒分流读者的情况下,《读书》的读者圈并不比1980年代小。我想是个硬参数,得先说出来。《书城》啊,《万象》啊,都是读书类型杂志,也发过很多有锋芒的文章,都很好看,但却分别面临了发行和经营的危机。这是另一个硬参数。
许纪霖:公共性解体背后还有一个技术手段的原因。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公共技术手段是印刷媒体,但今天,特别是年轻人,更多通过网络来了解这个世界,因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公共”,“公共”本身分化了。以前的中国知识精英有点像罗马教会,垄断了与上帝的沟通,像罗岗说的,通过《读书》来了解真理和知识。当年曾经流传过一句话:“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这就是“罗马教会”。但今天很多年轻人完全可以把“罗马教会”一脚踢开,直接同“上帝”对话。他们现在英语很好,可以直接读原著,理解力也不比我们差,在网络上形成了各种同龄人的小群体。最重要的,他们得先把我们这代“父亲”杀掉,然后才有出头之日。虽然在学术体制里边,他们不得不承受所谓代际之间的压抑,但是在网络公共空间里,他们没有“教会”,也没有“父亲”,享受真正的自由。这些都是文化思想巨变的一部分。
陈映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有些人说《读书》是社会科学化了、专业化了,所以难懂了。这有点误解了,社会科学如果能把问题讲清楚,为什么会让人听不懂呢?问题是社会科学需要研究者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同时需要写作者对问题有专门的研究。《读书》杂志这些年提出的一些问题很有意义,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许多问题在社会层面有一个大爆发,需要知识界、思想界作出回应。《读书》将中国问题放到世界的、亚洲的背景中去理解,也非常必要。但我作为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些文章看着不太舒服,不是因为觉得太专业化了,而恰恰是觉得作者或者是对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理解太任意,或者是对中国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有些不错的问题被提出来了,但议论却是在比较情绪化的,或者是在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展开的,这不利于真正的讨论的展开。我想这里面有一些原因,除了编者、作者的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较多埋头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缺少将中国问题与世界性问题对接、将具体问题提升到思想理论层面去思考的冲动或能力,也有的研究者是不习惯为学术刊物以外的杂志写文章。当然杂志可能也对社会科学界缺少相应的了解或互动。我希望《读书》杂志今后能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找一些真正对问题有研究的人来写一些给大家看的文章。
至于最近网上围绕《读书》的争吵,我个人感觉是看着挺悲哀的。如果说《读书》这些年来确实有转向,或者某种程度上存在共同体化的倾向,那么,一些知识分子和读者有“失家园”的感觉,这应该是蛮真实的。要害的问题是大家都缺少选择、缺少另建平台的可能性。现在别说另办刊物,就是以书代刊也困难重重。在这样的境况下,知识分子就只能为平台本身去争,相互耗,这真是可悲!
袁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在1980年代特定的环境之下,《读书》成了领头羊。那时候我们的意识也很简单,认为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时的思想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统一,看上去是统一,其实大家都没往深处想。随着走出国门的人多了,加上从国际上反馈回来,我觉得学术界最近十年是碎片化的时代,找不到统一大家的思想观念。从读者角度来评价,这十年《读书》给我的帮助很大,比如我比较欣赏冯象对法律的介绍,还有其它很多文章。我恐怕还想不出比《读书》更重要的杂志。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就算《读书》回到1980年代的风格,因为文学的边缘化,因为其它种种原因,它也不会达到1980年代的那种成功。
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思想和知识的新图景
张汝伦:1990年代以来有句话经常被人引用,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登场”。好像199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都以专业自负。但有个形象让我一直忘不了,就是英若诚在《围城》中演的高崧年说:“我是搞科学的。”那种志得意满的样子就同现在我看到好些朋友一样:我是搞考古的,我是搞古文献的,好像这样一来就有不容质疑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现在大学里大家都很强调专业,这没问题,可这个专业到底关心什么问题?你最后想说明什么?没有人问。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社会科学化非常糟糕,实际上是自然科学化。大家想一想,我们经常谈到马克思·韦伯。我们去看看他的传记,他一生关切着人类的问题、欧洲的问题、西方的问题、德国的问题,都是很现实的。但我们在专业性这样一种很漂亮的修辞和表达之下,缺失了我们对现实的关注。那么专业的内在动力究竟是什么?无非是在学术界扬名,掌握一些资源,然后做一个新的学阀学霸。
学术大跃进,最通常的产物是史。前几年,文学史估计有六十几种,哲学史也是这样。大家拼命地写,因为史是最容易的,你把材料堆起来就是一本史,可是一本史要探索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我对这几年的《读书》也有一点小小失望,与这一点有关系。有些人拼命地讲所谓学术本土化,我对这个口号倒不是很赞成,因为怕引起误解。但是谈一点学术的独立性怎么样?大多数文章是介绍这本新书,那本新书,这当然很需要。但对西方的学术工业缺乏反省和批判,就可能把一些非常不恰当的概念拿来用。比方说“世俗化”,比方说“重建公民社会”,比方说“中国没有公共空间”,这简直是开玩笑了。《读书》最要紧的是给人提供一个反省和批判的头脑,而不是仅仅简单地接受流行术语,和流行的事实描述。我们有那么多的现实问题,难道不能变为学术思考的动力?比方说一个人带着妈妈去看病的时候半路被人绑走了,去做砖窑工——我们当然不满足于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来思考它,但这件事情反映了1980年代以来整个思想文化发展里的某种缺失。我比较羡慕印度知识分子,好像他们比较有自己的话,这事情我们其实也可以做。
汪晖:我在这里说话不代表《读书》,只代表我自己。说到1990年代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时代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到来,或者说,二十世纪的终结。这不仅仅是说苏东瓦解、原来的计划经济破产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等等,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二十世纪曾经提供的各种政治模式几乎在今天这个时代失效了。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分化——贫富的分化、区域的分化、城乡的分化,这是一个重新形成阶级的时代,但你会发现,二十世纪以分化为特征的政治完全不能出现了。我在这里说的是曾经有效的阶级政治,比如工人阶级的政治,农民阶级的政治,不同阶级的政治,以及民族政治,比如反帝、反霸、反殖的政治,以及与这些相适应的方式、运动、理念以及组织,总之,构成二十世纪最大动力的社会运动、社会斗争、社会批判的模式,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了。我们今天有抗议,但不能构成二十世纪那种政治意识和政治运动。社会分层意义上还有阶级,但政治意义上没有阶级。你甚至可以说,有贫富分化,但没有分化的政治。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由于地位弱小没有产生出新政治,就连资产阶级、有社会地位的富人阶级也并没有浮现出清晰的政治意识。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1990年代代表了一个真正的转型,它意味着构成二十世纪的批判运动本身的政治模式虽然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经验,但不可能被简单复制。我们需要看到旧政治模式的失效,又通过历史的重新解读来形成新的可能性。一句话,我们必须想象和创造完全不同的新政治,才能面对今天的挑战。一方面是研究现实,一方面是解读历史,中国知识界的困惑跟这两面都有很大关系。
在1990年代,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是作为负面的、需要被告别的对象来加以处理。也正由于此,在知识领域,构成二十世纪政治的许多要素并没有被真正地作历史分析。很多人按照现代化理论研究商会、学会,其实不过是为了论证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的功能和作用,无法形成对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的新的把握。在这个时代,批判的前提也发生了很大危机,比如1980年代有两个主要的批判运动,一个是体制内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前者以异化理论批判社会主义体制,后者以价值规律的学说论证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长期共存的必要性;另一个是逐渐形成的体制外的新启蒙,它以介绍西方各种各样的知识为己任。这两个潮流的解放性和批判性均建立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统治的对抗之中。但1990年代以后,国家和政党本身发生了非常深刻的转型,简单的二元论已经无法把握今天的复杂现实和权力网络。不久前,印度知识分子查特吉在清华同我们座谈。印度最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在面临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过程时,也由于国家角色的转变而产生了分裂。要重新讨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护,就必然要重新讨论国家。原来最具对抗性的批判知识分子,忽然来重新讨论国家问题,在这个悖论现象中,他们发现原来的国家概念无法运用了,国家权力如今与资本、市场、全球力量相互渗透,我们应该从什么视野介入这个问题的讨论?再加上有全球化问题,霸权和战争的问题,它们与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的联系与区别何在?对于历史的再总结变得更加困难了。
历史叙述的合法性在今天关系到如何估价全球化、如何重新分析殖民主义历史、帝国主义历史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许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转化。二十世纪构成的明确的价值判断、是非领域,在这样的一个转化过程中模糊了。一方面讲左与右,一方面左右的界限变得非常不明朗。汝伦刚才讲西方的知识霸权,事实上重新叙述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变成一个问题。不光是概念,而且是怎么建立基本的历史叙述,这是价值危机的产物。经过了二十年的转变,我们变成没历史的人了;我们在不断叙述历史,但构筑不出一个真正的历史叙述,提供不了所谓价值图景。在这个背景下面,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所面临的危机其实是非常深刻的。中国知识界这些年的纷争,虽有很多不愉快的部分,但是透过这些纷争,我们多少发现有些东西在浮现,这是我从这些讨论中看到的最积极部分。比方说,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引导很多学生进入乡村,很多农民重新进行自我组织,很多历史资源就通过这样的讨论和相关的社会实践再次被提出来。对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而言,这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运动。没有这个自我教育运动,就没有重新叙述历史的可能性。2003年“非典”危机激发起的讨论也是这样。重新讨论医疗改革,一旦讨论深入下去,二十世纪甚至更早时期中国历史里的一些相关要素就被重新激发起来。哪怕这些讨论有意气用事之处,但由于问题的具体性,成果是积极的、主要的。有这样的争论比没有要好得多,有不同观点的具体分歧比简单地谈什么新左派、自由派也积极得多。通过这些争论,我们发现自己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刘擎:1990年代思想界争论很厉害,现在慢慢变得无声无息,回过头去有一点缅怀。有一个我称之为知识伦理共同体的东西正在坍塌,而学术与思想的虚假二元分裂,与这是有关系的。现在基本上是越来越恶化,既没有学问也没有思想。好像每个人都平等,但没有自我的政治主体性意识,用汪晖先生的语言,就是经过二十世纪一种很激动又很幻灭的东西,然后重新回到漫长的十九世纪。大家都慢慢成为一个工程化、技术化、指标化、高度生产性、完全空洞化的一个结构。我觉得应在大学体制里拯救一种批判的空间,然后在公共领域重新恢复一种思想生活,这可能比所谓新左派、新自由主义、传统主义这样的争论更重要。不管我们每个人有什么标签,其实对好多东西是有共识的。比如你对自由平等是不是接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谁不是批判知识分子和左派?比方说你是不是支持言论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谁不是所谓自由主义者?还有,你对高度商品化和工具理性化的世界是否警觉?在这个意义上谁又不是一个反现代主义者?
张汝伦:讲二十世纪也有一个问题:是谁眼中的二十世纪?我想起一千多年以前,朱熹为了和岳麓书院山长张 |
|
| 返回页首 |
|
 |
|
|
您不能发布新主题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编辑自己的帖子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删除自己的帖子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发表民意调查
|
|